Copyright ? 中國民間人才網 京ICP備2023017440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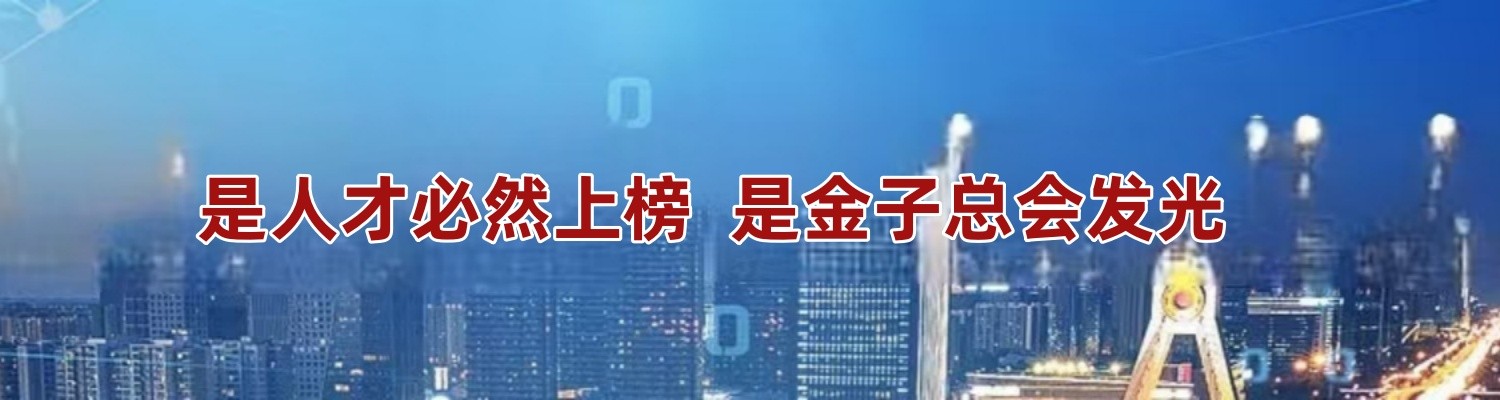

鄧紹寬(四川)


引言:小說根據《三聯生活周刊》人物新聞報道素材改編創作。以紀念我在山區與每月領七元補助的民辦教師一起工作生活的特殊歲月。
1994年的夏,像一塊燒紅的烙鐵,燙在成都平原上。火車站的喧囂裹挾著熱浪,知了的嘶鳴在油膩的空氣中顯得格外尖利。十八歲的艷敏,像一株剛抽穗的麥苗,青澀而脆弱。她緊緊攥著那張汗濕的綠皮車票,指腹反復摩挲著“臺江”兩個字,仿佛那是通往母親病榻的唯一符咒。薄薄的襯衫洗得領口起了毛邊,貼在背上,洇開一小片汗漬。三十塊工錢貼身藏著,沉甸甸的,是她剛在毛線廠用無數個日夜的疲憊換來的,能買藥,能買肥,能解家里的燃眉之急。
“妹子,找活兒不?”聲音像兩塊砂紙在摩擦。兩個穿著不合時宜花襯衫的女人湊過來,廉價的雪花膏味混著汗味,熏得人頭暈。胖的那個蒲扇搖得呼呼響,“電子廠,管吃管住,一月頂你干倆月!”
艷敏下意識地縮了縮身子,腳邊的蛇皮袋蹭著水泥柱,發出窸窣的聲響。里面是她全部家當:兩件舊衣,母親熬夜烙的紅薯干。“俺……俺得回家收麥子。”她聲音細弱,眼睛慌亂地瞟著檢票口上方的時刻表,心算著那趟歸家的長途車還有多久啟動。
“傻妮子!”瘦女人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力道大得像鐵鉗,“收麥子能掙幾個錢?你娘要是知道你能掙大錢,病都能好一半!俺侄女上月剛寄回五百塊呢,嶄新的票子!”
五百塊!艷敏的心猛地一跳。母親撕心裂肺的咳嗽聲仿佛又在耳邊響起,像破舊的風箱,一下下抽著她的心。那五塊藏在鞋墊下準備買冰糖的錢,此刻像塊烙鐵燙著她的腳心。她看著兩個女人“熱切”的臉,那熱切背后是深不見底的黑。嘴唇被咬出一道白印,她鬼使神差地點了頭。
走出站口的瞬間,一股熱風卷起地上的廢紙,撲在她的腳面上。她彎腰去拂,一張綠色的紙片卻從她敞開的衣兜里滑出,被風卷著,打著旋兒,輕盈地飄向遠處縱橫交錯的鐵軌,越飄越遠,最終消失在刺目的陽光里。像一只斷了線的風箏,再也尋不回歸途。
她不知道,那陣風,也把她吹向了命運的深淵。
一天一夜的火車在山區一個小站停了五分鐘,足夠一行人走出車站。拖拉機的突突聲在太行山的褶皺里爬行,像垂死的喘息。車斗里彌漫著羊糞、麥糠和汗液的混合氣味,熏得人作嘔。艷敏蜷縮在麻袋堆的角落,麥芒刺進脖頸,又癢又痛。暮色四合時,拖拉機停在一個被大山緊緊箍住的山坳里,黑黢黢的,像一口倒扣的鐵鍋。她被粗暴地推進一間低矮的土屋,門“哐當”一聲關上,緊接著是鐵鏈纏繞門閂的冰冷“嘩啦”聲,鎖死了她的世界。
黑暗里,只有自己的心跳聲在土墻上撞出空洞的回響。她摸索著墻角,指尖觸到一袋堅硬的東西——老鼠藥。三天水米未進,絕望像冰冷的蛇纏繞住心臟。她把那包苦澀攥在手心,像握著最后的選擇權。
門開了,刺眼的光線涌入。一個穿著打滿補丁藍布褂的老漢佝僂著背,手里攥著一個紅布包。他打開布包,一沓皺巴巴、沾滿汗漬的紙幣散發著陳舊的氣味。“兩千七,人我領走了。”聲音沙啞,像砂紙磨過木頭。他身后站著一個壯實的黑臉漢子,眼神渾濁,帶著濃重的酒氣,直勾勾地盯著她,那眼神不像看人,倒像在牲口市上估量一頭羊的斤兩——那是劉三。
她被劉老漢拽著胳膊拖出屋子。山石嶙峋的小路硌得她光腳生疼。她回頭望了一眼那間囚牢般的土屋,墻角那半袋老鼠藥像一只沉默的眼睛。她松開了手,任那包苦澀的粉末無聲地滑落在塵土里。被拐賣了。這個冰冷的事實,終于像淬毒的針,刺穿了最后的僥幸。
劉家的土坯房比關她的那間更破敗。屋頂的茅草稀稀拉拉,山風一過,簌簌地往下掉灰土。炕席破舊,散發著陳年的汗酸和霉味。劉老漢把紅布包往炕桌上一拍:“這是俺兒劉三,以后你就是他屋里人。”錢幣的邊角磨損得圓鈍,像被無數雙貪婪的手摩挲過。
“新婚”夜。一盞如豆的油燈在炕桌上搖曳,昏黃的光暈在斑駁的土墻上投下扭曲晃動的影子,像一張張無聲嘲笑的鬼臉。艷敏把自己死死地蜷縮在冰冷的炕角,指甲深深掐進掌心,用肉體的刺痛抵御著靈魂的撕裂。劉三滿身酒氣,踉蹌著撲過來,帶著牲畜般的熱烘烘的氣息。
“給……你給兩百,”他噴著酒氣,舌頭打著結,從臟污的褲兜里掏出兩張同樣皺巴巴的百元票子,在她眼前晃了晃,“你就能走。”
走,艷敏猛地抬起頭,眼中瞬間燃起一絲微弱的火苗,像溺水者看到浮木。
“真的”聲音抖得不成樣子。
“真的!”劉三咧開嘴,露出焦黃的牙齒,笑得猙獰,“可你有嗎?”
那簇微弱的火苗,噗地一聲,被這殘酷的現實吹滅了。她所有的錢,連同那張車票,都遺失在了命運的狂風里。眼淚毫無征兆地洶涌而出,不是因為自己的絕望,而是因為那五塊錢——那五塊本該變成母親嘴里一塊亮晶晶、甜絲絲的冰糖的錢!那甜味,成了此刻喉嚨里最苦的毒藥。
日子像村口那條渾濁的小溪,緩慢、凝滯,裹挾著絕望的泥沙流淌。逃跑的念頭從未熄滅。一次,趁劉三上山,她赤著腳,像受驚的鹿,沿著陡峭的羊腸小道狂奔。荊棘劃破腳踝,山石硌得腳底滲血。眼看山口在望,卻被兩個扛著鋤頭的村民堵了回來。
“買來的媳婦還想跑?劉老漢的錢是大風刮來的?”粗鄙的咒罵和推搡像冰雹砸在身上。她被推倒在泥濘里,冰冷的泥漿糊了一臉一身。
劉三聞訊趕來,手里拎著一根手腕粗的棍子,臉色鐵青。他沒打她,只是用那雙被酒精泡得通紅的眼睛死死地盯著她,那眼神像淬了毒的刀子,剜得她骨頭縫里都冒著寒氣。當晚,她的鞋不見了。她光著腳踩在冰冷的土炕上,腳底的傷口沾滿了灰塵和草屑,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死吧。這個念頭瘋狂滋長。
第一次,她摸到了灶臺上的鐮刀。冰冷的鐵器貼著腕部的皮膚,那里能清晰地感受到生命的搏動。母親的聲音卻在耳邊響起,遙遠卻清晰:“敏兒,活著,活著就有盼頭……”她的手抖得握不住鐮刀,“哐當”一聲掉在地上。
第二次,她找到了藏在灶膛角落的老鼠藥。那刺鼻的苦味讓她胃里翻江倒海。她閉著眼,抓了一大把塞進嘴里。苦澀瞬間彌漫了整個口腔,麻痹了舌頭。還沒等咽下,卻被進來拿柴火的劉老漢撞見。半瓢刺鼻的肥皂水被強行灌下,摳著喉嚨催吐,吐得膽汁都出來了,天旋地轉。
第三次,她撲進了村后冰冷的河水里。刺骨的寒意像千萬根鋼針扎進骨髓,瞬間奪走了呼吸。水嗆進肺里,火燒火燎地疼。就在意識即將渙散時,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了她的頭發,粗暴地將她拖上了岸。她躺在冰冷的鵝卵石上,望著灰蒙蒙、永遠也望不透的天空,只有冰冷的河水從發梢滴落,砸在石頭上,也砸在她死寂的心上。為什么連死,都這么難?
1996年的秋風吹黃了山里的樹葉,也吹來了一絲意想不到的“仁慈”。劉三突然說帶她回臺江縣紅苕溝探親。艷敏的心像被丟進油鍋,瞬間沸騰又瞬間冷卻。她連夜縫了個小小的布袋,把偷偷攢下的二十多個雞蛋拿到鄰村換了錢,仔細地縫進褲腰的夾層里。那點錢,是她卑微的希望,是通向自由的最后一張船票。只要見到爹娘,他們一定會救她!
推開那扇熟悉的、吱呀作響的院門,母親正佝僂著背坐在門檻上納鞋底。看見她的瞬間,母親手里的針線“啪嗒”掉在地上,渾濁的眼睛里先是震驚,繼而涌起滔天的悲慟。“崽啊……”一聲撕心裂肺的哭喊,母親撲過來抓住她的手,那雙布滿老繭和裂口的手顫抖得厲害,滾燙的眼淚大顆大顆砸在艷敏的手背上,灼痛了她的皮膚。
晚飯時,父親蹲在灶膛前,沉默地吧嗒著旱煙,劣質煙草的辛辣味彌漫在低矮的土屋里,嗆得人想流淚。昏黃的燈光下,父親臉上的溝壑更深了,背也更駝了。艷敏撲通跪倒在爹娘面前,積壓了兩年的委屈、恐懼、絕望像決堤的洪水,她泣不成聲,語無倫次地訴說著被拐賣、被囚禁、被毒打的非人遭遇。
母親把她拉進昏暗的里屋,油燈的光暈在母親憔悴的臉上跳動。“崽啊……”母親的聲音壓得極低,帶著無盡的悲涼和無奈,“人家……人家花了兩千七……那是多大一筆錢啊!再說……你這身子……結過婚的閨女……回來,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誰還要啊……”
每一個字都像淬毒的冰錐,狠狠扎進艷敏的心臟。她看著母親鬢角刺眼的白霜,看著父親被生活壓垮的脊梁,那點微弱的希望之火,徹底熄滅了。原來,家,也回不去了。她不再是爹娘捧在手心的閨女,而是被兩千七百塊買斷的、一件有了瑕疵的貨物。她默默地解開褲腰,掏出那個縫得緊緊的小布袋,里面是幾張被汗水浸得發軟的毛票。她塞進母親冰涼的手里:“娘……抓藥……”
母親的手哆嗦著,攥緊了那幾張皺巴巴的錢,淚水無聲地滴落,迅速在紙幣上洇開一小片深色的濕痕,像永不愈合的傷疤。
回下岸村的路上,破舊的長途汽車在盤山公路上顛簸。窗外,連綿的群山像無數沉默而猙獰的巨獸,張牙舞爪地向后掠去。艷敏靠著冰冷的車窗,眼淚早已流干,只剩下一種深入骨髓的麻木和冰冷。她看著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那張年輕的臉上刻滿了不屬于這個年紀的滄桑和死寂。她知道,就在這個秋天,那個名叫艷敏、對家和未來充滿憧憬的姑娘,徹底死了。活下來的,只是下岸村劉三的“屋里人”。
2000年的春天,下岸村貧瘠的山坡上,野山桃開得沒心沒肺,粉白的花朵在料峭的風里顫巍巍地綻放,給灰黃的山坳涂抹上一點脆弱的生機。村支書佝僂著背敲開劉家吱呀作響的院門時,艷敏正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給三歲的兒子喂奶。懷里的女兒裹在舊棉布做的襁褓里,小臉凍得通紅,像兩個熟透的小蘋果。
“艷敏啊,”支書蹲在門檻上,吧嗒著旱煙鍋,煙霧繚繞著他愁苦的臉,“村小的王老師……熬不住,走了。娃們……快散了架了。你……你讀過書,識得字,能不能……能不能去頂幾天?好歹……別讓娃們當睜眼瞎。”
艷敏的手頓住了,奶水濡濕了兒子的衣襟。她低著頭,看著兒子吮吸時滿足的小臉,聲音低得像耳語:“俺……俺不行。早忘光了。”她害怕。害怕站在人前,害怕那些或同情或鄙夷的目光,害怕那片小小的講臺會照見她靈魂深處無法愈合的傷疤。
“咋不行?”支書把煙鍋在鞋底上重重磕了磕,煙灰簌簌落下,“你看狗剩,丫蛋,都七八歲了,自己的名字畫得像鬼畫符!再沒人教,就跟咱們似的,一輩子困死在這山窩窩里,連個信都寫不明白!”
“一輩子困死在這山窩窩里……”這句話像一根燒紅的針,猛地刺進艷敏早已麻木的心臟。她想起了初中畢業時,班主任拍著她的肩膀嘆息:“艷敏,你是塊讀書的料,可惜了……”可惜了。這三個字,像命運的判詞,如今在這太行山的深處,又冷冷地回響起來。
第二天清晨,天剛蒙蒙亮。艷敏把睡眼惺忪的兒子交給婆婆,懷里抱著女兒,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向村東頭那間孤零零的土坯房——村小。推開吱呀作響、快要散架的木門,一股潮濕的霉味和塵土味撲面而來。窗戶用破塑料布勉強糊著,被風撕開的口子呼呼往里灌著冷風。所謂的黑板,是一塊刷了墨汁的破木板,早已斑駁龜裂。十幾個孩子擠在幾條破舊的長條板凳上,小臉臟兮兮的,身上的衣服補丁摞補丁,但那一雙雙望向她的眼睛,卻像山澗里未被污染的溪水,清澈,懵懂,帶著一絲怯生生的期待。
“老……老師好!”一個扎著稀疏羊角辮的小姑娘,丫蛋,怯生生地站起來,小聲喊道。
這一聲“老師”,像一道微弱的電流,瞬間擊中了艷敏。她捏著半截粉筆的手指猛地一抖,“啪嗒”,粉筆頭掉在地上,摔成兩截。她慌忙彎腰去撿,粗糙的土墻仿佛要將她吸進去。她深吸一口氣,強迫自己站直,顫抖著在黑板上寫下第一個字——“人”。粉筆劃過粗糙的木板,發出艱澀的“吱嘎”聲,留下一個歪歪扭扭卻無比莊重的印記。
沒有課本,她憑著記憶,把那些沉睡在心底的拼音、漢字、算術一點點喚醒,寫在黑板上。粉筆灰簌簌落下,沾滿了她的手指、袖口,像一層薄薄的雪。沒有教具,她用河灘撿來的小石子教孩子們數數,用樹枝在泥地上劃出“a、o、e”。她教孩子們念“天、地、人”,聲音起初干澀發顫,漸漸變得清晰有力。她教他們唱“東方紅,太陽升……”童稚的歌聲從破敗的土坯房里飄出去,驚飛了屋檐下做窩的麻雀,也驚醒了這個死寂的山村。
有一天,教到“家”字。她在黑板上用力寫下這個字,問:“娃們,你們的家在哪?”
“下岸村!”“劉家溝!”“后山洼!”孩子們七嘴八舌地喊。
只有丫蛋,低著頭,聲音細若蚊吶:“老師……俺想讓俺娘回家……”
教室里瞬間安靜下來。艷敏的心像被一只無形的手狠狠攥住,疼得她幾乎窒息。她別過臉去,手指用力抹過黑板邊緣的灰塵,指尖傳來粗糲的痛感,才勉強壓住眼眶里洶涌的酸澀。她想起自己遠在臺江縣紅苕溝再也回不去的家,想起娘塞給她的紅薯面餅,想起那張被風吹走的車票。放學后,她把丫蛋拉到懷里,從貼身的衣袋里摸出一顆用糖紙包著的水果糖——那是去年一個過路貨郎看她可憐給的,她一直沒舍得吃。糖紙已經磨得發毛了。“丫蛋,”她把糖輕輕放進女孩冰涼的小手里,“好好念書。念好了書,認得了路,長大了……就能自己找家。”
教書,成了艷敏灰暗生命里唯一的光源。這光,也在悄然改變著周遭的一切。劉三醉酒打她的次數明顯少了。有時她批改作業到深夜,他會默默地在灶膛里添把柴火,讓屋里暖和一些。一次,她發現教室的窗戶破洞被人用木板仔細地釘上了,雖然歪歪扭扭,卻擋住了刺骨的寒風。她問是誰做的,劉三悶頭劈著柴,甕聲甕氣地說:“風大,吵著娃們念書。”
村民們見了她,不再喊“劉三家的”或者“買來的”,而是帶著幾分生疏的恭敬喊一聲“艷老師”。初冬的一個清晨,她推開教室門,發現講臺上放著幾個還帶著泥土的蘿卜和一小袋金燦燦的小米。沒人說話,但那份沉甸甸的暖意,比任何語言都更有力量。她站在教室門口,看著孩子們在簡陋的土坪上追逐笑鬧,山風吹起她枯黃的發絲,也吹動了心底那潭沉寂已久的死水。她第一次清晰地感覺到,這片曾囚禁她、差點吞噬她的山坳,這片貧瘠的土地,用另一種方式,接納了她。而她,似乎也在這間破敗的土坯房里,在孩子們清亮的讀書聲中,找到了扎根的縫隙。那些稚嫩的聲音,像一顆顆渺小卻倔強的種子,落在她龜裂的心田上,也落在孩子們懵懂的心智里,等待著破土而出的那一天。
日子在粉筆灰的飄落和孩子們朗朗的書聲中流淌。劉三的變化是緩慢而堅實的。他不再酗酒,臉上的橫肉漸漸被風霜刻畫出些許溫和的線條。他開始笨拙地學著劈更細的柴火,好讓艷敏批改作業時手不那么冷。他甚至會偷偷觀察她握粉筆的姿勢,有一次,在油燈下,他拿著半截燒黑的木炭,在廢棄的煙盒紙上,歪歪扭扭地畫著“人”字,像一個最笨拙的學生。
2005年的秋天,山桃樹的葉子開始變黃。一個偶然路過的陌生人(后來知道是曲陽縣的農民攝影家向陽)被教室里傳出的讀書聲吸引。他站在窗外看了很久,拍了幾張照片。艷敏發現他時,他有些局促地解釋,說這景象很美。艷敏只是點點頭,繼續教孩子們念課文。她不知道那些照片后來去了哪里,也不關心。她的世界,就在這間土坯房里,在這些仰望著她的孩子們身上。
外界的喧囂終究還是來了。記者們扛著機器來了又走,問著千篇一律的問題。艷敏的回答總是很簡單:“俺就想讓娃們多認幾個字。”榮譽的光環(“感動河北”)曾短暫地籠罩過她,紅呢子褂穿在身上像一層陌生的殼。聚光燈下的掌聲遙遠而虛幻,遠不如丫蛋學會寫自己名字時那羞澀又驕傲的笑容來得真實溫暖。
光環之下,陰影也隨之而來。那些竊竊私語像山間的毒藤蔓,悄然滋生。她走在村里,能感覺到背后指指點點的目光。有次在河邊洗衣服,清晰地聽到石頭后面幾個婦女的議論:
“裝啥好人?還不是靠那點破事出的名!”
“就是!鬧得外面都知道咱村買媳婦,丟人現眼!”
“聽說上面撥錢修教室,誰知道進了誰的口袋……”
艷敏握著棒槌的手猛地收緊,指節發白,手背上的青筋根根凸起。一股積壓了十幾年的怒火混合著無法言說的委屈,像巖漿般沖上頭頂。她猛地站起身,河水打濕了她的褲腳也渾然不覺,朝著聲音的方向大聲喊道:
“俺被拐來鎖在屋里的時候,你們誰給俺遞過一碗水?俺被劉三打得半死的時候,你們誰攔過一句?俺在這破屋里教你們娃認字的時候,你們誰說過一句好?!現在倒來嚼舌根!俺艷敏行得正坐得直!這書,俺教定了!”聲音在山谷間回蕩,帶著一種從未有過的、玉石俱焚般的決絕和力量。那幾個婦女訕訕地閉了嘴,縮著脖子溜走了。
劉三不知何時站在了她身后不遠處的楊樹下,默默地遞過來一塊干凈的粗布毛巾。這些年,他學會了沉默的守護。艷敏接過毛巾,胡亂擦了擦臉,沒看他,也沒說話,蹲下身繼續用力捶打著衣服,水花四濺。有些隔閡,像山里的石頭,硬而冷,但共同經歷的風雨,也能在石縫里長出些沉默的苔蘚。
2014年,山桃花又開了,粉白如云。一位風塵仆仆的律師找到她,帶著一絲希望和更多的歉意。他告訴她,當年拐賣她的人販子,線索斷了又續,續了又斷,最終因為證據和時間(二十年追訴期)的問題……希望渺茫了。
那天傍晚,夕陽的余暉把群山染成溫暖的橘紅色。艷敏獨自坐在教室門口冰涼的石階上。晚風帶著山桃花清冽的香氣拂過她的面頰,也拂動了她鬢角早生的白發。她攤開手掌,常年握粉筆的手指關節粗大,指腹和掌心布滿了厚厚的老繭,像一塊粗糙的磨刀石。二十年了。她想起十八歲的那個夏天,車站喧囂的人潮,那張被風卷走的綠色車票,那個對未來還懵懂著、憧憬著的自己。
她抬起頭,望向教室。新裝的節能燈散發出明亮柔和的光,透過塑料布窗戶,照亮了里面一排排簡陋但干凈的桌椅,照亮了墻上貼著的孩子們的畫和獎狀——那是他們用知識和希望一點點裝點的“星空”。燈光穿透了山村的濃重夜色,比天上的星星還要溫暖、堅定。
她站起身,拍了拍褲子上的塵土,臉上沒有悲傷,也沒有憤怒,只有一種歷經劫波后的平靜和一種近乎虔誠的篤定。她推開門,走進那片明亮的燈光里。粉筆盒靜靜躺在講臺上。她拿起一支粉筆,掂了掂分量,然后轉身,在黑板上用力地寫下一行字,字跡沉穩有力:
“明天默寫:《我的家鄉》。”
窗外,山桃灼灼,在暮色中安靜地燃燒。山風依舊在吹,吹過沉默的群山,吹過簡陋的校舍,吹過孩子們夢想的嫩芽,也吹過艷敏染霜的鬢角。這風聲,不再是囚籠的哀鳴,而像一首深沉而悠長的歌,吟唱著生命的韌性與救贖——它講述著一個被折斷翅膀的靈魂,如何在最貧瘠的土壤里,用另一種方式重新飛翔的故事。她的人生,或許永遠無法逃離這口“鍋底的山坳”,但她親手點亮的那盞燈,卻照亮了一條讓孩子們走出去、讓希望走進來的路。這,就是她與命運抗爭的勛章,是她用血淚澆灌出的,最動人的人間真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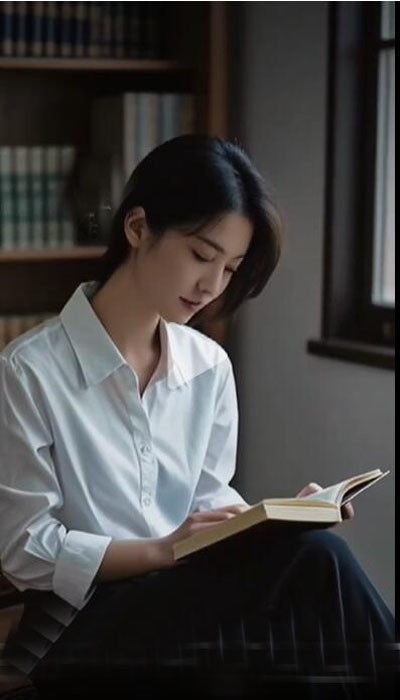



歡迎訪問北京智慧子月科技有限公司
熱點內容
Hot content
視頻推薦
VIDEOS